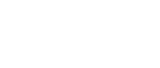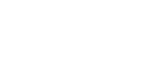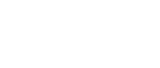生命的源头永远是故乡
| 招商动态 |2016-12-24
我的故乡是京广线上的一个小县城。有一个火车站,只一个大厅,集进站、出站、售票、候车于一体,每天有三五趟火车到站停靠。因为进厅就要进站,大厅的地基就修得很高,门口只好垒起长长的台阶,以至于站在台阶下,伸着脖子往上看,根本看不见车站的门。这有种神秘感,给背着蛇皮袋外出打工的人一种“拾级而上,自会平步青云”的幻觉。火车当然能把人带去一个精彩的花花世界,但从没走进过这车站的县里人肯定也不在少数。
县城北郊有个庙,供奉的人在远古历史上颇有名望,不少南洋的生意人都奉他为祖先,每年都不远千里前来祭典。县政府十分灵通,不仅每年都十分配合地组织大型庆典,甚至斥资修了一条大道,绵延十几里,从县城边界开始、横穿县城、直达庙门前。大道就以祖先的名字命名,每一路段都标上了路牌,这让外商十分满意,也让政府的招商引资任务圆满完成,皆大欢喜。好头儿开了起来,政府一无既往地好争个面子,县政府大楼的气派自不用说,大楼前修了巨型广场,挖了人工湖,湖上再建人工小岛,岛上再建古典小筑。这是北方,可这县城里偏偏有几个大小相连的湖,连同着护城河,政府把它们一水儿地绿化起来,全部走古典路线,奇花异草,雕梁画栋,各种健身器材、公益设施、形象雕塑、音乐喷泉一应俱全,顺便把护城河尾巴上的商业街也全部统一改造成三层的“仿古步行街”,尤其一到晚上,灯红酒绿,百姓出来聊天纳凉、吃喝消费,全县一片欣欣向荣的盛世景象。县里也打上了“北方水城”的旗号,制作了一张巨幅宣传画,立在高速路口上。
我们县多年来都是国家级贫困县。个别领导由于踏实苦干,深受人民爱戴,有年还上了央视新闻联播。北方水城是自己封的,毕竟北方多风沙,多数时候,整个县城还是灰扑扑的,路边稀稀拉拉的冬青蒙着厚厚一层土。仿古街头的空地又有外地人来开发,建起两栋几十层的商住两用楼,这可是头一份儿,三千多一平米,这还刷新了县城房地产的纪录。这楼一起来,顿时把只有三层的仿古街的光线遮了个严严实实,走在街上,总感觉天边几片乌云,让人透不过气,县城人还是太土,一下子适应不了水泥森林的新生活。
说到底,仿古街终究也开始没落了。以政府广场为中心的南城商业圈一日千里,居民楼一片片拔地而起,被收购了土地的城郊人乐开了花,住进了小区,拿到了赔偿款,正式成为城市“居民”了。——相反,老北城渐渐无人问津。从仿古待再往内城走一点,就是曾经远近闻名的马市街,要知道,马市街的名字在十几年前那是何等荣耀!只要想买东西,别管买什么,都得到这条街上来,这儿相当于县城的心脏!说从前,神气的老爷子们大晚上拎个马灯,优哉游哉地闲逛:我提着马灯逛马市街!嘿嘿!当年的老爷子们早已做了古,如今的马市街只剩下几家卖擀面皮、卖捞面的小饭馆,以及几家卖拖巴扫帚、鸡毛掸子的土产日杂店,前几年有人不识时务在这街上开了家大型超市,如今也是难以维计,灯都不愿多点,嫌白费电,昏昏暗暗地守着几个服务员,倒比顾客的数量还多。
马市街北街的尽头上分了岔,两个枝杈中间夹着的空地上是一个巴掌大的小庙,叫玄帝庙。不知道玄帝究竟是谁,只知道这是道家的庙,里面进出的人不是和尚,是道士。这儿的人爱烧香,管他佛家道家,一律都拜。这个庙有时也在门前搭台唱戏,戏种也多,梆子、四平调、大平调、坠子、道情戏,什么都唱,可没几个人听,虽然爱听戏的人多,可现在的老头儿都知道用唱戏机听戏了。音像店的售后服务极好,想听什么戏有专人负责下载好装进内存卡,听腻了再来店里换,在大街上都能听见精神亢奋的老太太在柜台前大声嚷嚷:“下错啦!我回去一听,这是四平调,我要的是大平调,大平调的《大登殿》!”
玄帝庙边上其中一条岔路口,是一个破旧不堪、似乎随时都可能坍塌的石牌坊,从牌楼下走进去,是一大片横七竖八、纵横交错、前勾后连、百折千回、复杂如迷宫、迂回如地道的巷子。
我家就在这巷子里。
这是典型的老城区,都是几辈子的老住户,汉、回、满杂居。马市街上就有清真寺,这儿回回最多。这好认,巷子里逛逛,不少住户门上都贴着回语春联。这边也有的巷子叫“胡同”,有秀才胡同,也有郎胡同。更多的巷子叫“街”。这里的小街小院不似北京的四合院,方方正正的阔朗院子,这儿土地紧张、空间拥挤,巷子本身都奇形怪状、时直时曲,院子就更是种类各异,让人叹为观止。有的外观似一户人家,等走进去才发现幽深至极,东拐西拧,一口气路过几十户,从后门出来时已经是另一条大街了。要说在巷子里迷了路,那可是非常有可能的事。
很显然,二十年前,巷子里的住户一脸骄傲地以“市民”自诩,现如今则成为县里著名的贫民窟,不少房子破烂不堪,风过掉瓦,云过漏雨。也曾有人想开发,可牵涉住户太多,赔偿代价过大,地段又不算好,想来想去,划不来。没人开发,日子只好就这么凑合着过下去。最有怨气的就是那些当年怀着市民憧憬嫁进来的城郊女人,到头来眼见着娘家的兄弟们占了地,赔了钱,住进了小区,只恨自己时运不济,气得天天骂娘。自从两年前这片区域被政府正式从“城关镇”改划到了“城郊乡”,居民们似乎一下子泄了始终挺着的那口气——还是认命吧。
骂人的只管骂,认命的只管认,日子还是得过。有个把飞黄腾达的,陆续地搬走了,剩下的老屋也难卖,只好任它破旧下去,巷子里常见这种久无人居、屋顶半塌、门窗长草的空房,拍鬼片做场地很合适。走惯了,不觉得阴森,小街里其实还是很热闹,没走的还多着呢。认命的那一群,含辛茹苦地养大孩子,有的翻盖了新屋,天台上种些花花草草,照样把生活过得有声有色。但小街里的热闹多半不是因为他们,过得好的都是偷着乐,热闹的是那群骂娘的人。这种大杂院本就容易吵架,住得太逼仄,家家户户檐牙交错,比如谁家修房奠高了地基,影响后院的视野;谁家后檐装了导雨槽,雨水流到别家院子;谁家山墙装了雨搭,侵犯了别家领空;谁家这月有客人长住却不肯多分摊水费;谁家往公共空地上倒垃圾……这时候各家的女人就会站出来开始激烈的“辩论”。一条街上的人基本都没有固定工作,无非做点见城管就跑的小摊生意,嘴皮子练得干脆利索,吵起架来个个都有泼妇的阵势。本来家道艰难,关系切身利益当然更要寸土必争。居委会明察秋毫,对辖区情况了如指掌,无论是当年的计划生育大行动,还是现在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名额,全都采取了相互举报有奖金的政策,一群街坊大义凛然,挺身举报,没有一个该罚多领者漏网。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,在这里完全不适用。
我家所在的巷子在外围,再穿一条官驿街,往右一转,就是大桥头。一家所有的衣食住行、柴米油盐的消费都能在这里解决。桥没有名字,可只要一提“大桥头”三个字,县里所有的出租车、蹦蹦车都会准确地载你来这儿。桥下的河水几近干涸,近年来的填河盖房都快挤到河中心了,一股沉淤缓静的黑水安卧在桥下,顺着我家街后一路铺展过去,河滩一度是我童年的乐园。桥的另一头就是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,它们则主载了我的少年读书时代。现在坐到家中,偶尔还能隐约听见学校里的广播体操,让我一阵怅然。
我家这条巷子全长不过百余米,按门牌数有二十多户。门牌按“U”形排列,我家在十号院,也就基本排在巷子的尽头。街面上还算宽敞,可以擦着墙勉强通过一辆面包车,当然这是在没有任何对头车的情况下,因为就算迎面过来的是一辆自行车,除非自行车自觉往后退到巷子外,否则面包车是绝对过不去的。家家墙下都种了几棵植物,把屋檐下的这点宝贵土地充分利用起来。无非是些月季、瓜菜、爬山虎,还有汪曾祺写过的晚饭花,晚饭花这里叫烧汤花,因为在这儿做晚饭一律称“烧汤”。一路看过去,一街绿莹莹的墙角,显得桃红李黄、春意盎然。——至于生活其中的人呢?不好说,因为评定的标准不好说。印象里,总觉得这些巷子是属于女人们的,反正我的记忆里总是冒出一个又一个女人。
隔壁十一号院有个姑娘,长得白白净净、眉清目秀,可偏偏遗传了母亲的软脚病,生下来腿脚就是歪的,且严重O型,走路一崴一崴。姑娘很争气,读书一口气读到大学毕业,就业时自然麻烦,待业几年,姑娘不服气,又拿起书开始复习考研。可想而知,复试总是过不了。她始终不愿认命做点裁缝类的工作,只是一味看书,爹妈管顿饭吃还管得起。谈婚论嫁的时候自然又是高不成低不就,时光磋砣,成了个紧锁深闺的老姑娘。她真像旧世闺秀,从来没见过她和谁说过一句话,也从来没见她有过任何喜怒的表情,除了去巷尾的公共厕所之外,她几乎不出屋门,年深日久,皮肤愈加苍白,白得像画中人。每次遇到她,我都替她忧愁一阵,总觉得她有很多故事,或者心事,可这故事和心事,未免也太平淡。
七号院有个倒霉的可怜女人,本是妯娌两家和婆婆住在一处,她生性愚钝懦弱些,正是大观园里二姑娘迎春的软面性儿,嫂嫂偏又伶俐能干,和婆婆合起伙来欺负她,轻则白眼,重则谩骂,像佣人一般对她呼来喝去。她生了个儿子,丈夫又死了。儿子偏又在七八岁上得了尿毒症,只好以医院为家,一天天熬。精神的长期压抑下,她居然变得痴痴呆呆、半人半疯。有时在门前看到她走过,瘦小得简直不像成年人,她看到我了,用极缓慢的速度扭过头来,怔一会儿,又用极缓慢的速度转过头去,那呆滞的、卑怯的、枯朽的眼神,一度让我想起祥林嫂。不说她也罢。
另一个女人住我家对面,十四号,叫香果,从农村嫁进来,男人是某厂的工人,比她大十几岁,没什么大出息,守着几百块钱工资度日,她就做做清洁工,去商场停车场看看车。要说日子紧巴,只要平平安安,怎么着都能过,可贫贱夫妻百事哀,连着生了两个女儿之后,男人日渐不满,天天逼着她生儿子。实在是养不起了,用香果自己的话说:“他四十多的人了,也不看看这屋里除了四面光墙和漏雨的屋顶,还有哪样东西养得起仨孩子的!”后来还是又怀了,香果前思后想,自己偷偷去打掉了,回来后又是一场大闹。她是那种十分擅长表演的人,前一秒还在门口欢欢喜喜地逗着小女儿玩,后一秒马上就红了眼圈,诉苦连连。我爱莫能助,临了扯了院墙上的丝瓜豆角送给她,她千恩万谢地拿去了。不料我母亲听了之后说不让我送,因为香果每天凌晨四五点就来我家外墙偷偷摘菜,明着送了还会让她误会。我很气愤,觉得被她愚弄了,母亲却说,她也确实困难,摘就摘吧,随她去,我们只当没发现。后来我回家小住,她听说我在北京,马上跑来让我帮她大女儿解决工作,说在物流上做分捡员太脏太累,想让我在北京帮她找个办公室里的工作。我真是哭笑不得,不知道该怎样和她解释。有时想想,也许她的两个女儿将会延续她的生活轨迹,变成另外两个香果。
最后说九号院吧,一大家子都姓范,多年前突然搬来老两口,说是范家的表亲,老爷子当年赴湘教书,一去就安了家落了户,老了老了,总想着落叶归根,退休后就带着湖南籍的老伴回来,可亲族都已失散,只好在这表亲的院里盖了房子,安顿下来,一住就是十年。那位湖南老阿姨是小学教师退休,很爱说话,和我母亲很聊得来,她们都算是这街里的“高级知识分子”了,大概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,我读中学时放学回来总见她们坐在屋里聊天。她有两个女儿,一个外孙,大女儿离异,所以都带过来一起住着。两位老人都经历了曾经的动乱年代,见识过风浪的人,格外珍惜美好生活,每日里她家厨房里飘来的湖南式的变态辣味呛得人直咳嗽,然后就听到她满街里喊她的外孙:“阿威!阿威!吃饭!”这也是典型的南方名字,这儿可没人叫“阿”的。老阿姨把家收拾得很漂亮,门口的小水缸里养着黄灿灿的金鱼,窗户上吊着蕾丝的布幔,这让从小生长在棚户区的我艳羡不已,尤其是她小女儿有架钢琴,一度让我神往。好日子过了几年,她大女儿的婆家突然寻了来,闹腾着还是把她亲亲的外孙阿威领走了。这才让人恍然大悟,他们离乡背井也有这层躲避的因素。她大女儿也是十分漂亮的湘妹子,始终没有再嫁。又过几年,老爷子得了癌症,治了,然后没了。老阿姨失魂落魄,抱着原想落叶归根的老伴的骨灰盒,还是回湖南去了。
老阿姨的故事说完了,可她留下的那套两层小楼却注定要酿就一场争夺战。最有竞争力的这个老范,两个儿子都不成气,可不成气也有比较级。老大在厂里当电工,也生了一个儿子,日子过得去,只是爱喝个酒,一旦醉归,六亲不认,当街撒泼,揪着老婆的头发打,老婆也不示弱,和他对着打。老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,偶尔帮人卸卸货什么的,挣顿饭,挣条烟,条件远不如老大,偏偏一气儿生个双胞胎,俩儿子。老婆又爱跑爱玩,整天忙着打扮,一双孩子扔着没人管,一睁眼就哭闹要东西吃。老二总想打老爹的主意,下了狠话:“你再不给我钱,我就卖儿子!”老范也不恼,不紧不慢地答话:“你想卖一个就卖一个,你想卖一双就卖一双,我就这点钱,不留着养老,难道等着让你养我?”老范的老伴爱跳舞,跳着跳着,一把年纪,居然和人家跑了,他心里的气儿也正不顺呢!
争到最后,还是老大有底气,出了一些钱,明正言顺地要了那套房子,欢天喜地地乔迁新居。过上几年,没了老伴的老范也过世了。没了老爹,老二家境每况愈下。大年二十九,老二出去喝酒,当娘的出去打牌,双胞胎在自家床上点火玩,被子着起来,木床也着起来。孩子见火大,跑出来街上玩去了,直到老大家的儿子看见火光嚷起来,四邻才陆续知道。这时候人们都在家,不缺人手,接水的,提供器皿的,打119的,出来看热闹的,围了半条街。消防车也到了,巷子太窄进不来,消防队员背着器械一个个挤进来,就连瘸腿的深闺姑娘都出来看了,可见盛况空前。这时候火焰早已从窗口扑出来,像迎风旗帜一样翻飞招展,等老二两口子赶回来,他们的家已经名符其实地“家徒四壁”了。家没了,女人大概觉得再无留恋之处,直接收拾东西走人了,老二索性把孩子扔给嫂嫂照管,惹得老大老婆天天在院里骂。奇怪的是,老二的女人并没有走远,常常在前面官驿街能够见到她,当街拉着人的自行车后座不让走,笑着骂,显然是老相识。看到她,我总是想,如果时代变迁,也许她会成为《状元境》里的三姐,有一堆一堆的风月故事要讲,只是我们无缘知道。
老巷子里的人和事这样杂乱无章,没个头绪,理不出个所以然。都说当局者迷,可能也是我无从解释的原因之一。如今我已离家多年,漂来漂去地辗转几个地方,这才渐渐明白,原以为的天经地义可能只是一乡一俗,原以为的人间真理可能其实荒谬无理,原以为的稀松平常也可能是难能可贵,也正因为对故乡心怀了更复杂的心情,这才了解憎恶之何以憎恶,悲悯之何以悲悯。我十八岁之前都生活在这里,它是我生命的源头,它永远具有辐射我的能量,影响我对世界的认知和判断,我必须承认,我无法拒绝。从前总以为可以轻易地换个地方,重新生活,但现在我知道我的思维方式永远是俗的、入世的、闹哄哄的、热闹中保持着笙歌散后人世凉薄的清醒,说白了,总归是红尘中的人,红尘中的生活,逃不开,躲不掉,放不下,忘不了。从此我不愿书写悲剧,想看悲情的故事,生活本身就是,何必再去编造。我更愿意和妇孺老少看戏一样,看个才子佳人,看个金榜题名,看个欢天喜地大团圆。
游子总把自己比作离开故乡的一片云,渴望有一天重新飘回故乡的天空。于我而言,故乡本身就是一朵云,它自在随意、漫无目标地飘着,本没有荫庇滋养谁的冲动,这几年飘得离我有些远,也不知道它会继续飘往哪里去,但不管怎样,抬抬头,总能远远地望见。浮云蔽白日,游子不顾返,我与它相看不厌,却又各自安然。我有时会深情地怀恋它,但更多时候,会像一个寡恩的旧情人一样追忆它,就像周朴园终年关闭着窗户,追忆那个为他生了孩子的鲁侍萍。不知道年老心倦时,我会不会也渴望叶落归根,就算是流落江湖,载浮载沉,那一片幽深如迷宫的巷子必当在我记忆中化成与天地联通的管道,滤去所有的苦难和伤痛,析出滴水成珠的凡尘水晶。
原创文学 欢迎转发
阅读之后,
愿享同感。
西子榆
 招商热线:400-151-2002
招商热线:400-151-2002